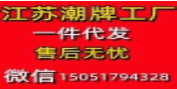互联网夺不回客厅
-
-
类目:电商运营
-
联系人:
-
微信号:
-
Q Q 号:
-
手机号:
-
浏览量:
377
【商户信息】
【货源详情】
如果连“客厅”都正在消失的话,那么“客厅经济”则成为一个伪命题。
很显然,如果有人试图解释“客厅”的空间价值和文化功能,答案并不唯一。但衔接和纽带,或许是两个重要的隐喻。在这个半开放的空间里,私密与社交缠绕,集体与个人共享,祖辈的旧时代与未来的新事物碰撞,电视直播、家庭影院、在线视频、主机游戏、K歌、VR……在以“家”为单位的建筑有机体里,我们能想象的最大限度进行交互与娱乐的场所,不约而同都指向了客厅。
于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客厅”场景成为了新消费的必争之地。“客厅经济”、“大屏时代”、“客厅争夺战”等关键词也迅速加热,行业赛道的预言图景值得畅想:新客厅经济将会成为下一个新的产业爆发风口,掌握了家庭的入口,也就掌控了市场的未来。
但是与之矛盾的现实场景是,我们正越来越少地踏入,使用,甚至停留于客厅。客厅,好像成为了一个留守场所,老人和孩童,是他们最后争夺的用户。作为家庭的入口和纽带,客厅场景在一年之中的高光展现,几乎只剩下除夕夜合家团聚观看一场春晚的时间。
5G时代,智慧家庭确实正在崛起,但与之对应的,其实是客厅意义的消解。而真正的“客厅经济”,非但没有到来,也许正渐行渐远。
01
客厅角色的演变
salon,即为法语中客厅的意思,中文里音译的“沙龙”一词,也正是由其演变而来。
文艺沙龙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是17、18世纪西欧上流社会的一种精英社交文化。当时的沙龙常在贵族的客厅中举行,社会名流们聚集在此朗诵诗歌,探讨文学和艺术,交流着凡尔赛语法。后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沙龙又逐渐演变为哲学政治俱乐部。总而言之,此种语境下的客厅,是名副其实的社交场所。
在沙龙文化影响下,中国也曾诞生过一个颇有话题度的“客厅”——太太的客厅。
在冰心女士那篇醋意弥漫的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中,讲述的正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接待朋友的“客厅”。在此出没的,既有金岳霖、钱端升、陈岱孙等政治、经济学家,也有像沈从文这样的知名作家,还有萧乾、卞之琳等在学大学生,全都慕名而来。
这个位于北京布胡同3号院里的客厅沙龙,回响着高谈阔论,誉满京城,象征着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顶峰。
当然,这个维度上的“客厅”并不属于普通老百姓,也只是短暂地辉煌过。
随着报刊等大众媒介的普及,咖啡馆、音乐厅等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客厅偶然承担的这种公共叙事空间迅速开始坍缩,精英范式的社交功能也被更多元化的公共领域平台取代。而沙龙,选择了其它更自由、开放的举办地点。
扯掉小众的知识贵族光环,客厅的主旋律依然是回归家庭,并且是整个家里的重中之重。
在20世纪80年代,一套60平建筑面积的典型住宅里,客厅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5平米,放置了沙发、茶几、电视柜、冰箱和可折叠的餐桌等,而且客厅的沙发还常为沙发、床的两用型,充分展现了客厅区域活动、休息、会餐的多重功能,是集吃、住、行一体的综合体。
当然,还有会客。即客厅保留的社交功能——接待身边的朋友,或是远道而来的亲戚客人。在多世同堂依然很普遍的环境下,亲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当社会和科技在飞跃,更多的新技术、新事物开始涌现和更新,而住宅的空间处理也趋于细致,结构更加现代化,设计调度更追求人性化。比如过去常位于客厅的冰箱,后来多搬入厨房;而餐厅的出现也标志着客厅内就餐功能的消失。
生产力的驱动也产生了心理需求的变化和升级,回到家中,人们更希望客厅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客厅的功能,逐渐从实用意义转向精神层面。而这个精神的窗口,由电视机打开,文娱影像内容走到中心。
有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在中国城乡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阶层中,黑白电视、小尺寸彩色电视与大尺寸彩色电视处于多样化的并存形态。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电视机前,一家人坐在一起,每晚准时收看7点的新闻联播,或者守着电视台的八点档电视连续剧已经成为那时人们晚间休闲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客厅的“纽带”作用如此紧密。
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属于客厅的黄金时代,那一定是VCD/DVD年代。
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并不智能甚至略显笨重和粗糙的影碟机,却迸发了巨大的能量。它对客厅而言带来的价值,对用户习惯的培养和文化冲击远远超过后来那些五花八门的互联网电视盒子。
1993年,世界上第一台家庭VCD影碟机在中国诞生。此后便形成了一个持续近十年、年销售额数百亿的影碟机产业。
在1994年至2010年间,中国本土与中外合资的相关企业,一共在中国生产了至少7亿台LD、CD、VCD和DVD播放器。短短十余年间,VCD及DVD影碟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总体销售数量,几乎没法统计。
影碟机及影碟,为电视开辟了新的播放时间与观看方式。播放碟片,可以选择适当的时候开始或暂停,摆脱了电视节目在时间流程上的固定性,更具有及时性与私人化的特征。现在看来,自由点播、选择内容等等,已经是我们观看视频很基础的习惯和要求,但在当时,影碟机显然是中国当代影像受众走向类型化的一个有力建构者。
90年代兴起的录像厅,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大量在国内电视台和电影院无法看到的海外影视作品。而影碟机,将这一可能搬进了家庭,搬进了客厅。一套港台武侠连续剧或最新好莱坞大片,甚至是情色音像内容,可以像普通电视节目那样供家庭化的群体在厅堂之间、斗室之内共同观赏。
也正是在VCD/DVD的电子消费热潮下,走出了最初的“家庭影院”。
电影院由放映厅、影院设施、播放设备三大部分组成,家庭影院也是一样。播放厅就是家中的客厅,影院设施是客厅中的沙发、桌椅等,播映设备则由一套完整家庭影音系统组成,主要包括AV扩音机、音箱、大屏幕电视机及激光影碟机等。
而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内家庭影院产品一般都有卡拉OK功能。毫无疑问,卡拉OK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是惊人的,于是在一个小小的家中,既能收看电视直播,又能观赏到世界各国最新的电影,还能聚会K歌……客厅承担着多功能娱乐的角色,完美演绎了互联网时代前的家庭C位。
然而在辉煌的反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至2003年,全国共查获各种侵权盗版走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六亿多张,平均每年约为六千万张。在这个属于客厅、属于沙发的DVD黄金年代,中国也成为了同时期全球盗版最严重的国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影碟机和传统电视机迅速走向衰落。互联网革命的骤变不仅更新了物与技术,也更新了生活的方法论,和人们对内容的理解与认知。
于是,继智能手机后,电视也不得不智能起来——人们开始在电视机上接入互联网。
02
IPTV与OTT,临近尾声的客厅“争夺”战
国内传统电视厂商与互联网企业很早就开始前仆后继地尝试生产“能上网的电视机”,但2013年是个分水岭。
这一年,乐视宣告以互联网超级电视杀入客厅,创造了“49分钟1万台X60被抢购一空”的销售记录。同年,小米科技也正式推出了搭载安卓系统,能够提供30多万小时正版高清内容和具有追剧功能的“新小米盒子”,第一版的小米盒子曾因有悖于181号文件精神而被广电总局叫停。
盒子这种东西早已有之,我们也并不陌生。有线电视网络成为主要传输方式和数字电视兴起后,电视机由“一体式”变为“分体式”,成了“电视屏+机顶盒”。机顶盒俗称“盒子”,是一个连接电视机与外部信号源的设备,可以接收来自有线电缆、卫星天线、宽带网络以及地面广播的信号,并能接入互联网。
在争夺战的初期,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通过派发机顶盒就轻易抢占了客厅。2010年年初,中央将“三网融合”、“媒体融合”、“互联网+”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通信运营商们利用IP专网和专用机顶盒开展视频业务的IPTV快速发展。几乎你只要去营业厅办理网络宽带,运营商肯定会给你捆绑出售一个电视机顶盒套餐。
2013年以后,乐视盒子、小米盒子、天猫魔盒、华为盒子、百度电视棒等互联网OTT盒子相继登场,一时间,似乎所有企业都在疯狂推销盒子,客厅的战争进入“发盒”时代。
尽管通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发的盒子都接入了互联网,能看到更多在线视频和点播节目,甚至打开其盒子,都有游戏、音乐或者教育产品等其他应用,但两者的业务形态却有所不同。三大运营商的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业务是指运营商在宽带公网的基础上建立了IP专网用于承载IP化的数字视频内容,需要使用运营商的盒子或专属网络路线;而OTT(互联网电视)业务是以Internet公网为承载,连接普通的网络即可,当然,使用其看电视的时候会占用带宽。
更通俗来讲,IPTV会有直播信号,OTT没有。打开电信发的机顶盒,你能直接观看CCTV-1等频道的电视直播,但是天猫魔盒不能。以前,用户还可以在互联网盒子上下载直播应用,只需要购买一个互联网盒子,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就能够实现网络视频和电视直播的观看。
但互联网公司加入盒子大战以后,国家广电总局开始对OTT TV业务实行监管,禁止OTT盒子提供直播服务,并通过牌照方等一系列播控政策对大屏业务实行严格管控。
按照正常的逻辑,有人或许会怀疑,没有了直播业务的OTT缺乏竞争力,但现实却是,IPTV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急剧萎缩,而OTT却呈现了绝对的增长。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的人们没那么爱看电视了。这里的电视,首先就是指电视台放送什么观众就收看什么的电视直播。
IPTV虽然理论上也能浏览网络上的在线视频,但其内容数量,收费模式,甚至页面显示都是相对落后和古旧的,使用感非常“不互联网”。所以电视直播也是它的唯一优势,或者说价值。
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在上面追一部芒果的新剧,你需要在IPTV的芒果专区订购专门的产品包,如果你想看一部热门的好莱坞电影,你需要订购另一个影视产品包,只要你选择购买,这些产品包可以直接从你的话费账单里扣。
听起来似乎和互联网的流媒体会员差不多,实则不然,你订购的都是运营商的增值业务包,钱并非直接交到内容商手里,而是由运营商和内容商进一步分成,大头都流入了运营商的口袋。你也并非某视频网站的会员,你只是能在这个宽带账号下,这个机顶盒打开的这台电视机上收看这部内容。
更为特殊的是,由于IPTV业务都是由各个省级的运营商提供,比如四川电信、辽宁联通,内蒙移动等等,而各地的发展状况和政策存在差异,所以不同区域的IPTV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低线级城市、西部及华中地区等市场用户更多、收入更高。在有些省区,甚至还没有落地爱奇艺或者腾讯等专区,其引入的内容,不够新也不够热。
即使是有这些头部内容集中的网络视频专区,时下的跟播内容从互联网平台更新到IPTV平台也往往存在延迟,丧失了一些时效性。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行业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用户2.74亿户,互联网电视(OTT)用户8.21亿户,此时的运营商已经落后两倍不止。
除了少数家中的老人还会打开机顶盒上收看地方电视台,或者央视8套热播的一部战争片,而由这些老人陪伴的孙子孙女或许也会因为年幼不懂事,在上面随意订购一部动画片,IPTV争夺的用户已经所剩无几。
而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年轻一代的文娱生活,视频会员制也培养了如今绝大多数人的内容付费习惯。人们更愿意在这些流媒体网站充一个会员,追剧,观影,自由选择视频内容,自由发表弹幕评论。电视直播是什么?或许他们只会在除夕夜的春晚时刻才会想起来,然后跑去哔哩哔哩蹲守了B站春晚,完成了新时代的“守夜礼”。
多数受众从客厅大屏收看的不再是直播电视节目,而是各大视频网站OTT端以点播为主的电视节目或网络视频节目。传统电视台不再是客厅大屏的主角,流媒体视频内容在大屏场景中成功“篡位”。
而OTT用户规模保持增长的另一个因素还在于智能投影的入场。“盒子”终归是传统电视厂商适应互联网、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产品”,只是为互联网“入侵”客厅经济提供了入口。互联网当然不会满足于“发盒”,各大厂商和互联网公司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智能电视一体机的军备赛。
但历史潮水滚滚向前,电视机的颓势已成必然。
从2018年开始,我国彩电市场已出现连续三年量额齐跌。奥维云网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达4450万台,同比下降9.1%,零售额规模1209亿元,同比下降11.7%。但另一边,根据洛图科技《中国智能投影零售市场月度追踪》报告,2020年中国智能投影市场销量为372万台,同比增长15%,销额为87.8亿元,同比增长12%,2018年至2020年,家用投影仪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6.6%。
大屏的数量仍然在增加,但同样是互联网电视,人们不再钟情于鸡肋的盒子或是花里胡哨的智能彩电,而是转向了更具现代感的投影设备。
于是互联网公司又开始争夺属于投影仪的蓝海:百度领投极米,阿里领投坚果,腾讯力推极光,还有小米、联想、创维等IT数码、彩电以及传统投影品牌纷纷入局。
从“盒子大战”、“内容大战”到“终端大战”,这场属于客厅电视大屏的争夺,看似互联网已然全胜,宣称他们占领了大屏幕,找到了客厅新的增长点。但传统电视机或者电视台的退场,其实更多意味着传统内容和传播方式的落幕,这种变化的本质是家庭生活方式的更迭,而前者正是“客厅”的生活方式。
尽管电视大屏的设备形式越来越多,但电视机的开机率一降再降,已成无法挽回的定局。2017年以来,日均开机率已经从70%下降到了30%,智能电视粘性较高,但也只维持到51%。
虽然大多数人都是通过OTT收看网络流媒体内容,但大屏播控政策还存在着各种限制,比如爱奇艺在电视端需要改名为奇异果,而电视端和手机端/电脑端/PAD端也往往不能共用一个会员,大屏侧的会员必须单独购买,有些人宁愿直接把手机上的会员视频内容投屏到电视上。
当然,对于另一部分年轻人来说,电视机还可以充当别的容器,比如用来连上PS4或者switch主机打游戏。
但比起大屏,现代人显然更依赖手机小屏。他们的内容获取,信息来源,社交网络,甚至会员,全都来自于那个指尖可触的小屏。于是互联网电视把更多小屏上的内容和APP搬上了大屏,甚至有微博、淘宝、短视频等等。你开始说不清,互联网在客厅争夺的核心究竟是哪个屏,好吧,最终他们告诉你这是多屏时代。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用户使用时长提升为互联网第一,竖屏内容的发展速度一骑绝尘。而与此同时,对年轻人而言,电视大屏,沦为了游戏机或者手机的显示器。
人们确实没那么爱看电视了,这里的电视,也泛指所有电视原生的娱乐内容。
只有在那个以电视机为内容中心的年代,家庭成员被吸引在一块屏幕前,荣光才属于客厅。
03
从智能音箱到loT智慧家居
互联网对客厅的奋力一搏
如果把电视大屏作为客厅经济的主入口,那么互联网显然还想从各个角度“包超”和“围猎”客厅,不遗余力地贩卖了其他各种智能产品和方案,试图打造一个未来的多功能客厅。
2016年,“互联网女皇”、KPCB合伙人玛丽·米克尔有过一个预判:“语音拐点已经到来。”
于是从智能音箱开始,互联网宣布客厅进入语音唤醒时代。
智能音箱,在传统音箱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技术上具备WiFi连接,可进行语音交互;二、功能上,可提供音乐、有声读物、信息查询、O2O等互联网服务,以及场景化智能家居控制能力。
国内厂商中以喜马拉雅的小雅为代表的智能音箱,以内容分享为主,将音箱作为音乐、有声读物等流媒体内容的载体。还有一种是以亚马逊Echo为代表的智能助手类音箱,以语音交互技术为重点,可以成为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国内互联网想厮杀的显示是这一种。
对于客厅场景而言,智能音箱想解决的是人与家的交互的问题,其第一属性是智能,而非音箱,因此智能音箱主流玩家都是互联网公司,而不是传统音箱巨头,因为前者拥有AI技术、互联网内容与服务资源。
于是京东的叮咚音箱,阿里的天猫精灵,小米的小爱同学,百度的小度音箱等等,互联网科技巨头们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智能音箱大战,推动了中国智能音箱市场的高速增长。
来自IDC的数据显示,互联网巨头进入音箱补贴战后,2018年,智能音箱全年出货量突破2000万台,同比增长1051.8%;2019年出货量达到4589万台,同比增长109.7%。
以智能音箱为载体,你可以接入家里的空调、空气净化器、智能电视、扫地机器人、智能窗帘,智能门锁和智能照明等家居设备,通过语音来控制任何家里的电器家具。
互联网迅速升级为物联网(loT),在万物互联的新时代,一切都可以变得智能,甚至是一盏床头灯。
于是战火迅速蔓延到了智能家居,成为新客厅经济的争夺关键。
从智能家电单品,到成套家电智能,再谋求全屋智能家居的落地,随着5G牌照的发放和落地,客厅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科技感和智慧性。5G至少10倍于4G的峰值速率、毫秒级的传输时延以及百万级的连接能力,承诺我们不仅将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同时还会满足未来万物互联的应用需求,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与影响。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包括5G、IoT、云服务、大数据、边缘计算等等都在为智能家居赋能。在巨头们描绘的生态网络里,未来客厅或许是这样的。
开门智慧解锁一瞬间,客厅的灯光、玄关的鞋柜自动打开,电视智能开启并调至常看节目。窗帘、扫地机器人等都可语音控制,而且互相联动,比如,在客厅说一声“我要洗澡”,热水器会自动加热到习惯温度,并可播放你喜欢的音乐,而快洗完时同样只要一句话,卧室即可调至舒适温度,避免浴后着凉。洗完澡后,浴室自动开启全空间排湿,而洗澡前丢入洗衣机的换洗衣物,也已洗净并自动烘干。
残酷的是,这一切对现在而言,或许足够智能,但并不那么未来。原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被颠覆,甚至也没有实现几十年前科幻电影里就已经被全息投影包围的赛博空间幻想,人与互联网的交互只需要通过思维,所想即所现,所感即所得。客厅里的智能音箱也没有承担起类似《钢铁侠》中贾维斯的,真正意义上全方位的AI管家功能。
智能家居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客厅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和飞跃,依然被硬件禁锢,实现的可能只是语音和定时。
但现实往往是,智能产品买了,App也没少装,但生活就是没有智慧起来。而对用户来说,用手机APP可能并不比找遥控器更便捷。统计显示,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都沦为了一个摆设,手机APP激活联网不到20%。
而未来的“智能”还如此脆弱,断网就瘫痪,断电就宕机,一旦品牌与其它品牌连接还会变成“智障”。由于大多数智能家居是依托于电源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所以在停电以后基本上无法再进行操作。家里停电的时候,你的灯具还是需要手动打开,而你的智能窗帘也许动手都拉不上。
当然,智能家居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有部分行业领先者或许已经可以实现断网甚至断电后的自动化。但如果只是将所有的硬件产品智能化连接起来,那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新客厅经济”的宣传而言,如何主动满足用户的需求,去升级和丰富生活体验,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数据曾经预测,作为部署物联网的关键,中国智能家居的设备需求量将在2021年超过智能手机,显然有点“赶英超美”的意思。
但据IDC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累计出货1.56亿台,同比增长36.7%。2019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量突破2亿,达到2.08亿台,较上年增长33.5%,增速已然放缓,而智能手机的销量尽管连年下滑,2019年国内的出货量也在3.72亿部。
进入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各行业波动较大。但随着疫情隔离等政策的展开,居家时间延长,按理应该是loT高速发展的时间窗口,也是客厅经济的增长机会期。智能家居市场却出现了负增长,仅以2020年第三季度为例,设备市场出货量约5112万台,同比下降2.5%。智能音箱的出货量约829万台,也同比下降14.7%。
除了疫情因素,上游元器件短缺和消费者本身购买欲望的下降是重要原因,智能家居市场在初期的爆发后整体进入了调整期。以小米为例,根据2020年财报,小米IoT与生活消费品的同比增速下滑,总收入占比较2019年也下降了2.8个百分点,预示着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的“极速狂飙”或许已经告一段落。
除此之外,互联网科技巨头在客厅场景,也面临着永恒的不信任问题——数据泄露和隐私安全。
尽管科技厂商一再否认通过智能音箱、语音助理或者其他智能手段收集数据和用户隐私对话,但事实是,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裸奔”。作为私密的家庭场景,智能家居更加值得人们小心。
“基于家庭模式,你可以了解用户的行为。”你的智能门锁在分析人脸,智能摄像头在监听对白,即使是灯具也能构成一个家庭生活的地图,它透露出的信息包括:用户几点回家?孩子几点就寝?用户是否喜欢熬夜?
作为智能音箱“销冠”,亚马逊Echo智能音箱和其语音助理Alexa就曾多次曝出用户语音记录泄露事件,国内外许多互联网大公司都面临数据安全的质疑,此外,隐患还来自多如牛毛的小微硬件。《2020物联网安全年报》披露,去年未被业界识别的物联设备就新增了50万个,安全状况可想而知。
大量的设备在激活,越来越多的用户数据在云端储存和交互,隐私与安全是当务之急。
智能家居常见的安全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APP隐私数据采集和上传;另一类是由于家电端缺乏安全保护手段, 造成家电端的程序或是储存的敏感性数据被有心黑客恶意破解, 从而导致WIFI密码外泄, 仿冒设备接入或者入侵等更为严重的现象。
以往传统家电、家具都是沉默的,而智能家居这种可联网、可存储、可计算、可执行的新型范式本身就要建立在用户的生活习惯之上运作,互联网显然不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保障隐私数据是封闭的,不会被加以利用,并且还存在着很多安全漏洞有待解决。
智能家居增速放缓的背后,消费者心理也可以在此追溯一二,除了并不够智能,人们或许并不愿意用家庭隐私去交换一个智慧客厅。
在使用手机连接智能家居设备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信任,不再开放如地理位置、麦克风等权限。
当我们像“透明人”一样暴露在科技面前,我们至少希望在客厅,在卧室,在自己的家里是安全的。
04
如果我们正在“失去”客厅本身
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互联网大谈“客厅经济”如何如何的时候,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正在失去客厅本身。
根据自如与新华网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目前,中国城市的租住人数已超过2亿人,其中55%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26-30岁的租客占比达到31.48%,00后租客的占比超过5%。
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出走异乡,在都市漂泊,能有一个落脚歇息的场所,交通便利,通勤时间不要太长,点外卖送达时间不会太久,已经是一种宽慰。
介绍时,他们通常会说我租的房子在哪里哪里,离地铁站很近,而并非我家在哪里哪里,客厅很大。
因为整租与合租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差,另一份《2020中国青年居住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城市中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的青年人,有8成选择了合租。
对于城市打工者来说,在合租居住模式中,最重要的是提供休息睡眠的场所,也就是一张床。除了休息行为外,洗漱和洗浴行为也是合租房内频率较高的居住行为,因此,年轻人在租房时对卫生间状况也会重点考虑,如厕、洗漱等功能的正常使用,还有其舒适性和作为公共空间的尴尬程度。而客厅的使用率在合租房中是最低的,也是租房人群对房屋整体考量的末位因素。
996、KPI、内卷,每天被工作和压力填满,上班——地铁——下班——廉价的城中村出租屋,每一天都是如此循环,简单机械枯燥的生活让人麻木,回去了也只想躺着刷手机。很多女孩子加班太晚,回到住处往床上一趟,没卸妆没换衣服就睡过去了。作为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的客厅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存在感,和利用价值。
即使出租屋里有一个客厅,也形同虚设。没有人会在那活动,也很少会把朋友叫过来玩。一想到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不熟悉的人,就注定这是个没有生活的客厅。
而很多在北上广合租的年轻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客厅,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的房东将客厅改造成隔断间,又可以多一个住户,从而消除了客厅。
房地产开发商在设计、建造房子的时候,考虑的是整栋房屋的格局组合与消费人群的匹配,如loft公寓是卖给单身青年,两室一厅是卖给三口之家。
然而在一线城市,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和高企的房价使得这种“精心的安排”付之东流。房东或二房东将一套房子尽可能的隔断成更小的单位,租给多的人,赚更多的钱,从而去追求一种在商业地产才常用到的概念——“坪效”。
当一套房子寻求“坪效最大化”的时候,客厅往往成为最先牺牲的部分:它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同时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北京,有的房东能把一套180平的的房子隔断成8个房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还有很多年轻人正在租着从阳台隔出来的单间。
如果是情侣合租,或许情况会好很多,至少客厅不再是一个完全闲置的状态。但以使用频次来看,客厅也完全不是什么互联网必争的消费场景,更不用说让他们为智能家居这种客厅经济买单。
即使是夫妻或者家庭的自购房屋,“客厅”格局本身在室内设计中的分量也越来越轻。传统客厅的位置开始在家装图纸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甚至“消失”,很多人不再砸重金装修一个“客厅”,让其承担家庭核心入口的重任。
沙发+茶几+电视机老三件的固定搭配被摒弃,过于笨重的沙发和堆放杂物的茶几不再受到欢迎,电视柜更是早就被淘汰,许多业主干脆敲掉了电视墙。人们对屏幕的热情逐渐转向投影后,用户也更倾向于把小巧的投影仪搬进卧室。
对于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还会把休闲区搬进阳台或者独立的娱乐空间等,甚至为原先散养在客厅的宠物打造专属的宠物房间。客厅原本承载的功能被转移,被放弃,具体的布局由用户喜好量身定制,比如安放书柜书架,或者打造成健身区域等等,符号化的空间让位于生活。
“去客厅化”的背后,不止是科技变迁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更新,也是由于客厅的本位意义是从家庭出发的,而传统的家庭模型和家庭观念正在瓦解,甚至连家庭也开始失重。
2020年,基于公安部的初步数据,中国出生人数下降了15%,一些城市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3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正在试验各种激励措施,例如税收减免、增加教育和住房补助金以及育儿假等。
但是在短期内,恐婚恐育仍是很多年轻人的现状。老龄化加速,生育率下降,离婚率再创新高,固定程式的家庭模式被逐渐解构,人们越来越不喜欢一个标签化的客厅。
各种渠道和口号都在宣传新客厅经济,然而不论是电视大屏还是智慧家居,互联网试图争夺,或者说目前能够想象并触及的,可能一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旧客厅。
AI、5G、IoT等技术的发展,新基建的政策红利,确实正在加速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我相信物联网是未来的方向,也期待智慧家庭生态体系,带领人们探索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但事实是,人们或许不再需要一个客厅来连接人际情感和巩固家庭关系,而那些种类繁多的新产品、新场景是否真的寄生于客厅,未来又是否与客厅有关,不得而知。
彼得·戴曼迪斯在《创业无畏》中说,“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创造一个未来。”但他们显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未来。互联网试图探寻客厅场景的流量池底,或者努力旁敲侧击一些新的入口,市场仍然会有增量,却不可能夺回属于客厅的黄金年代。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关于互联网客厅的船票最终可能都通向孤岛。